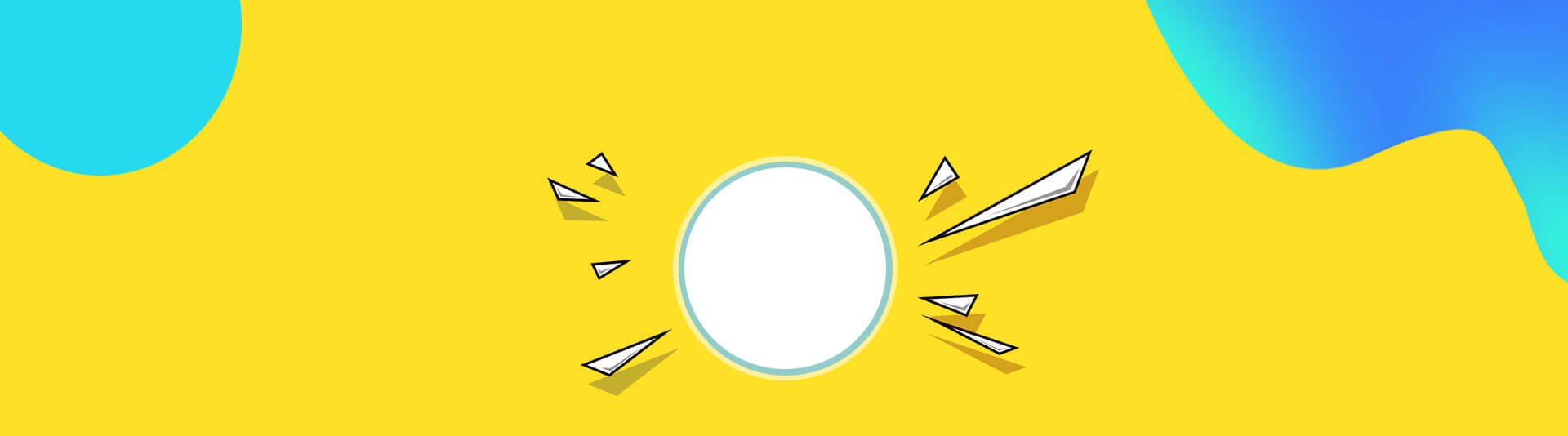当时中国读者热衷于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智斗的故事,在馀生的小说《智斗》(1923年连载于《台南新报》)中,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甚至远赴中国台湾,开始了一场新的较量◆★■◆◆■。按照吕淳钰的研究,这部小说显然是对亚森罗苹巴黎故事的模仿,然后将其原样挪移至台湾。比如小说中的嘉义不过是巴黎的替代品,八掌溪则可以视为塞纳河的镜像之物。本文所选的第一幅图像■★◆■,即是小说《智斗》首次在《台南新报》上连载时的版面截图■■★。
一方面,本专栏主要关注福尔摩斯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现象,比如《老残游记》中的人物竟然也会开口便提到◆★■“福尔摩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作者们热衷于书写◆■“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滑稽故事;福尔摩斯在当时不仅是文学人物形象,更进入到媒体与商业领域,成为小报名称与香烟品牌;改革开放之初,叶永烈将侦探与科幻相结合,创作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续写■■“香港福尔摩斯■★”的传奇……
孙了红《侠盗鲁平奇案》封面,上海万象书屋出版,中央书店发行■★■◆,1943年10月初版。
关于小说中有着★■■◆■◆“东方亚森罗苹◆★■”之称的主人公罗平,张碧梧基本上是把他作为一名中国传统侠客的形象来进行理解并塑造的。比如在小说《双雄斗智记》中,罗平自己就曾经说过◆★◆:“我的为人你向来晓得,我虽是绿林中人,做的是强盗生活,但天良未泯,事事都凭着良心★■。■■◆◆★◆”他完全是将自己放置在■■★■■◆“天良未泯”的★◆★◆★■“强盗”与■◆■★◆★“绿林中人◆★◆★”的人物序列之中进行自我认知与定位的,而这基本上可以视为对《水浒传》与《三侠五义》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与人物形象的一种延续。又如◆★◆,小说里罗平的助手分别叫做什么“草上飞”★◆◆■◆★、“冲天炮”与“急先锋”,也完全是一派《水浒传》式的人物起姓名绰号的风格★■★★★■。此外,在小说每期连载最后,也经常会出现诸如“下回书中自有分晓”这种传统章回说书体小说中才会用到的★■◆“过场词”。总体上来说,张碧梧是借助了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写法和思路来重新理解并书写了这个■■■★◆■“东方亚森罗苹”的故事。但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这部小说中同时又出现了电★★、汽车、密室机关等现代化的物质设备和科技想象★■◆,和传统的小说人物与故事风格之间形成了某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1925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周瘦鹃■■■、张碧梧、孙了红、沈禹钟等人用白话译的全二十四册的《亚森罗苹案全集》,收二十八案,其中长篇十种,短篇十八种■◆。这是继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之后,中国侦探小说翻译界的又一件大事。到1929年12月,该书已经印至第三版。而在1942年,上海启明书局又一次推出了《亚森罗苹全集》。可以说◆◆■◆◆,对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翻译、出版和阅读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作为小说译者的包天笑甚至不惜通过贬低福尔摩斯来提升亚森罗苹的形象和地位:★◆★“福尔摩斯不过一侦探耳,技虽工,奴隶于不平等之法律★■★◆■■,而专为资本家之猎狗,则转不如亚森罗苹以其热肠侠骨,冲决网罗,剪除凶残,使彼神奸巨恶,不能以法律自屏蔽之为愈也。★■★”(包天笑:《亚森罗苹案全集序》)◆◆。相对而言★■★★◆,作为民国时期亚森罗苹系列小说最重要的译者周瘦鹃,很早就敏锐地指出了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各自背后微妙的民族身份象征:“英伦海峡一衣带水间,有二大小说家崛起于时★■★◆■■,各出其酣畅淋漓之笔,发为诡奇恣肆之文■◆■。一造大侦探福尔摩斯,一造剧盗亚森罗苹。一生于英,一生于法。在英为柯南道尔,在法为马利塞勒伯朗★★■★。”(周瘦鹃:《双雄斗智录第四十九》★★◆■,载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也就是说■■,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个人智力的比拼,更涉及英法两国民族情感的问题◆■,作为当时国际舞台上相互较量的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英国人发明了大侦探福尔摩斯■◆,那么法国人就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捉弄并打败福尔摩斯的侠盗亚森罗苹◆■。
和程小青创作“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即后来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情况相类似,民国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标为“东方亚森罗苹★◆◆◆■”的小说★★■■■◆,在这些众多的模仿者中,有五种“东方亚森罗苹◆■■■”系列侦探小说影响力最大,其作者分别是张碧梧、吴克洲、何朴斋、柳村任和孙了红。这里需要注意的事情有三:一是这些◆◆“东方亚森罗苹”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曾经是大东书局亚森罗苹小说的翻译者,比如张碧梧和孙了红■◆■★■■;二是他们笔下的侠盗人物往往和亚森罗苹有着姓名发音上的高度相似性,比如鲁宾★■★★、罗平或鲁平◆■◆■■;三是和法国亚森罗苹智斗英国福尔摩斯相类似■★◆,这些“东方亚森罗苹”也需要一个对手,而这个想象中的对手,就经常是程小青所创造的“东方福尔摩斯”霍桑。
如果说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侦探小说,除了福尔摩斯探案之外,就首推侠盗亚森罗苹系列小说了。而说到莫里斯勒伯朗笔下的亚森罗苹,当然和福尔摩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诸如《亚森罗平智斗福尔摩斯》及其他很多故事,甚至可以视为福尔摩斯的“同人”小说。柯南道尔生前还曾经对此表示过不满,莫里斯勒伯朗为了避免版权纠纷,也特地将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尔摩斯)改为更具法国特色的Herlock Sholms(赫洛克修尔梅斯),将Dr.Watson(华生医生)改为Wilson(威尔森),将Baker Street 221B(贝克街221B)改为Paker Street 219(帕克街219号)■◆★■,但读者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真正的所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专著或专栏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译、创作、评论等文学形式与文字内容固然是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基础——本专栏更多关注图像文本与形式,试图从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资料入手,来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本专栏名为“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其实是从★◆★■◆“画◆■■■■◆”入手,追溯历史时间线索(所谓■★■◆■◆“连环”),借★■■★“画”说◆◆“话”。
甚至中国第一篇亚森罗苹小说的翻译引进,也一定程度上借助此前福尔摩斯小说翻译的流行◆◆■◆■★。1912年4月杨心一在《小说时报》第十五期上发表了小说《福尔摩斯之劲敌》,其原作为1907年出版的Arsene Lupin,Gentleman-Cambrioleur,而在这篇首次被引入中国的亚森罗苹故事,标题中出现的却是福尔摩斯的名字,不难想见当时中国译者与读者在接受亚森罗苹这个新的文学人物时,有着强大的福尔摩斯阅读前史作为背景和支撑■★■。之后十年间,经由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张舍我等译者的不懈努力,大约有20篇亚森罗苹系列长短篇小说分别经由法语◆■、英语和日语等不同路径被陆续译介进入中国◆◆◆★◆■。(具体参见姜巍:《民国侦探小说〈亚森罗苹案全集〉译本来源考》★★◆◆◆◆,《新闻出版博物馆》,2023年第3期)
当然,民国时期更著名的★◆◆◆■“东方亚森罗苹”形象还要首推孙了红笔下的鲁平,和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相类似,孙了红的侠盗小说创作也经历了从早期模仿勒伯朗到后期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到了40年代◆★■★■,孙了红的小说就不再被称为◆★★◆“东方亚森罗苹案”,而是具有了更强的本土IP属性和名称——“侠盗鲁平奇案”。孙了红本人也和程小青并称“一青一红★★■◆”★★,共同构成了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两座高峰。本文所选的第三幅图像就是上海万象书屋1943年出版的小说集《侠盗鲁平奇案》的封面,画面中血手★■■◆★、手枪与人头、剪刀与被剪的纸人、■■■◆“33”的数字,分别代表小说集收录的四篇作品《鬼手》《窃齿记》《血纸人》和《三十三号屋》★★◆◆★★。而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中◆■★◆◆,孙了红也会极力凸显他笔下人物的外在特征,比如鲁平自称“侠盗★◆”,有着绝对醒目和与众不同的“商标★★★”——永远打着鲜红的领带,左耳廓上有一颗鲜红如血的红痣★◆,左手戴着一枚奇特的鲤鱼形大指环,酷爱抽土耳其香烟等等。甚至在1989年的电影《侠盗鲁平》中,电影海报直接用一顶礼帽和一条鲜红的领带来代指鲁平的人物形象,可见孙了红当初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深入人心◆◆■■。
自从1896年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2010年以来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在百年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显影◆◆★”◆★◆★■★。
张碧梧模仿亚森罗苹大战福尔摩斯的系列小说所写的《双雄斗智记》(最初连载于1921-1922年)是民国时期难得一见的中国本土长篇侦探小说,本文所选的第二幅图像就是该小说单行本初版时的封面。在这部小说一开篇■■◆★★,张碧梧就清楚地交代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所依据的故事来源:■★◆★“今者东方之福尔摩斯既久已产生,奚可无一东方亚森罗苹应时而出,以与之敌★■■■,而互显好身手哉◆■?★■■★■”一方面张碧梧创作的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结构是在模仿勒伯朗的小说★★◆,写一个中国版的亚森罗苹大战福尔摩斯的故事;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所设立的想象中的对手正是程小青所创造的“东方福尔摩斯”霍桑。小说单行本封面上的两个人物,持手枪向上瞄准的人是罗平■■◆★,而举起双手的人就是霍桑。
只可惜■■◆◆,创造出民国时期最具风采的侠盗人物的畅销小说家孙了红,生活上却相当窘迫,不仅只能寄居租住在最廉价的亭子间,还在咯血症病发时没钱医治,只能依靠朋友和读者的“众筹◆■★■■★”与救济而勉强度日。小说里的侠盗鲁平与小说外的作者孙了红,构成了一组深刻的反讽——侦探与侠盗不过是想象中的英雄罢了。